煮酒读书 || 汉末酒酣悲歌起
中国古代,王公贵族在宾宴、婚娶盛会之时,席间要做木偶戏表演,酒酣之后,奏乐高歌。宴请、婚礼这种喜庆的宴会上,所用的音乐和歌曲也都是喜庆的。但到了东汉后期,自大将军梁商起,画风为之一变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,在东汉永和六年三月上巳日 (公元141年),大将军梁商大会宾客,于酒阑戏罢,他歌唱了一首挽歌,名叫《薤露》,闻者皆为掩涕。
梁商唱的《薤露》和另一首《蒿里》,当时都是送葬时候唱的挽歌,据史料记载,它们出自于秦末山东的豪士田横,当时田横羞于臣服汉高祖刘邦,自杀而死,他的门人为了纪念他,为之做挽歌,意思是感慨生命之无常和短暂。
《薤露》大概的词意是:“薤上朝露何易晞,露晞明朝还复滋,人死一去何时归。”《蒿里》大概的意思是:“蒿里谁家地,聚敛魂魄无贤愚,鬼伯一何相催促,人命不得少蜘蹰。”至汉武帝时,乐师李延年将其再编曲,在葬礼上使用。送王公贵人时唱《薤露》,送士大夫和庶人时唱《蒿里》,这是挽灵柩者的歌词,当时称之为挽歌。
梁商在东汉当政的外戚里,是有贤名之人,“史有令誉,严谨自持”。但在上巳宴宾之节,他忽然将本来送葬的挽歌,引入喜庆的宴会中,可能来自某种难以名状的预感。
梁商的即兴感慨悲歌,没想到居然演变成了全社会的时尚,到汉灵帝当政时,京城里在请客宴席、婚宴上做木偶戏表演,酒酣之后续以挽歌,成为一种时尚。稍晚,学者应劭认为:在宾宴、婚礼宴席这种原本喜庆之时,唱挽歌绝非吉祥之音,“自灵帝崩后,京师坏灭,户有兼尸,虫而相食”,就是在喜庆宴席上唱挽歌的后果,将挽歌引入喜庆宴席,这是一种末世征兆!但应劭的看法,在当时并不是主流的观点,同时代文治武功皆为的曹操,依然继承了挽歌的传统,以《薤露》《蒿里》之曲做诗,我们现在知道《薤露》《蒿里》的歌词内容,即来自于曹操的《薤露行》和《蒿里行》两首名诗。不过曹操所描述的真的已是非常悲惨的局面了,在《蒿里行》他这样写道: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,生民百遗一,念之断人肠。”其时,曹操已经是亲自在战场上厮杀的军人,经历了朝出可能夕不归、随时战死沙场的血火经历,已经没有了应劭那种谶纬迷信。在他看来,生与死全凭天命,跟唱什么歌、喝什么酒毫无关系。他几乎把每一场酒宴都当成生离死别,进而慷慨悲歌,也由此将挽歌转化为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“建安风骨”。
添加18202991745邀请加入李寻交流群
此风延至魏晋,名士颜延之酒店裸袒挽歌;《后汉书》作者范晔夜中酣饮,听挽歌为乐;大诗人陶渊明干脆给自己做了三首挽诗,而且成为了千古名诗,其中有名句为:“亲戚或余悲,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所道,托体同山阿。”大诗人看淡生死,的遗憾是“但恨在世时,饮酒不得足”。
汉末魏晋之际,悲凉的挽歌冲入喜庆的宴席,随后演绎出三国、魏晋长达数百年的离乱。悲惨的现实生活和无奈的慷慨情绪,充盈了那一个时代的文学史。对此段历史往事系统的梳理,来自于宋亚莉博士的大作《东汉晚期士人活动与文学批评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6年出版)。
宋亚莉博士是1982年出生的一位年轻学者,我感到惊奇的是:这位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往事居然有如此刻骨的认识和感受。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年轻学者里难得一见的著作,书中对东汉晚期的时事和诗人风骨有多方面的描述和解读。深夜捧读此书,不得不数次起身煮酒,以平复起伏不定的思绪。
推荐资讯
- 婚宴用酒怎么选择呢?2020-09-01
- 瓶装酒存放必须要知道的细节 !2020-09-01
- 散酒中存在哪些重要指数?2020-09-01
招商推荐

- 原浆进口OEM贴牌葡萄酒
- 类型:
- 热度:

- 我要加盟
- 白酒动态
- 啤酒动态
- 红酒动态
- 到东北喝了顿酒,才知道为啥东北白酒走不出东三省,不是价格问题
- 东北酒商30年启示录|中国酒业(漠河)大会⑥
- 跟东北人喝酒,别动不动就说“我干了你随意”,要记住这3个规矩
- 东北酒商30年启示录|中国酒业(漠河)大会⑥
- 郭嘉文开美甲店生意火爆,在维港豪宅内宴请宾客,李泽楷未现身
- 金华婚宴习俗争议!酒店上菜顺序致宾客提前离席
- 泰方回应军官宴请中国贵宾事件,国防部强调符合外交惯例
- “希璞酒店”重磅招募30家合伙人,纽宾凯酒店集团发布“凯宴计划”
- 金华婚宴习俗争议!酒店上菜顺序致宾客提前离席
- 泰国军官国防部宴请中国游客引热议,泰方回应称系VVVIP礼宾接待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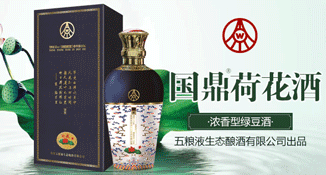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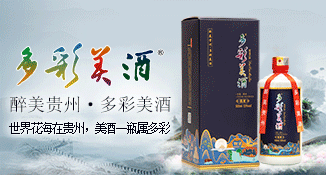


我要加盟(留言后专人第一时间快速对接)
已有 1826 企业通过我们找到了合作